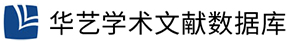| 题名 |
Traditional Chinese Legal Thought |
| 并列篇名 |
<商君書>內的法理思想 |
| DOI |
10.6199/NTULJ.1995.24.02.02 |
| 作者 |
張偉仁(We-Jen Chang) |
| 关键词 | |
| 期刊名称 |
臺大法學論叢 |
| 卷期/出版年月 |
24卷2期(1995 / 06 / 01) |
| 页次 |
47 - 86 |
| 内容语文 |
英文 |
| 中文摘要 |
法家思想淵源甚爲深遠,<尚書>及<左傳>內就記述了許多統治者的立法、司法事跡,甚至湯武革命也稱爲「恭行天之罰」。但對此等行爲給以理性的詮釋,則在春秋之後,而以商韓二人留下的著述最多。 商鞅之時封建制度快速崩解,政治核心日益衰微,傳統的規範失去了約束的力量,以致戰亂不止,許多國家的君主被權臣篡殺,土地被強鄰併吞,所以商鞅認爲當時治國的第一件要務就在鞏固中央政權。他並且提出了一套社會演進的理論,以說明此一主張的必要-據他分析,人類必然經過「親親」、「上賢」及「貴貴」三個階段。在他的時代,諸「賢」並起,是非莫辨,必須要有一個強大堅定的君主,以專制的手段加以裁斷才行。這樣的君主應受人民絕對的服從,享有至高的尊貴。 誰能成爲這樣的君主?商君認爲他應該具備兩個要件:第一要有高度的智慧,第二要能「博力」,能「殺力」一增聚並利用國力•這樣的君主去那裹找?商鞅沒有說明。儒家也期望有特別智慧能力的聖君來治理國家,而他們所說的聖君是可以由一般人中培養出來的;商鞅沒有談到教育和自修,所以我們只能推定他的聖君和道家墨家的聖人一樣,都生來如此的天縱之聖。 當然商鞅也很清楚大多的統治者都不是聖君,但是他的理論必須有一個聖君,所以他對於「如果統治者並非聖君該怎麼辦?」這個問題,並無妥當的答覆。 如有了一個聖君,他應該做些什麼?商鞅認爲當時的亂源在於社會上有著許多有害並互相矛盾的觀念、價值和導向,使人陷於迷惘、徬徨和不斷的衝突之中,無法集中力量做任何一件事,所以他認爲君主的首要任務是要建立一套全國一致的價值、目標以及是非的準則。這一點是莊子以外各家共同的看法-孔子的「正名」、墨子的「尚同」、老子的r法地、法天、法道、法自然」,目的皆在於此。不同的是各家的價值、目標、準則以及如何建立其價值、追尋其目標、適用其準則的方法。 商鞅要建立的價值很單純;只是國家的富強。其理由也很簡明一國家不富則兵力不強,兵力不強「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侍」,結果必定「土地侵削」,國家滅亡。相反的,如果國家富強,便可「兵無敵而令行於天下」。這似乎就是商鞅的終極目標了,至於「令行於天下」之後,將使天下如何,他沒有說明。 怎樣才能使國家富強呢?商鞅認爲必需要求全國人民從事農墾和戰鬥。農墾可以創造財富,人民樂於從軍作戰可以使國家兵力強盛,都是顯而易見的。 但是當時的人並不完全同意商鞅的看法,他們還認可並追求許多其他的價值和目標,例如知識、道德、利祿等等。所以社會上有許多「詩書談說之士」、「處士」、「勇士」、「技藝之士」及「商賈之士」。 在商鞅看來,這些價值和目標對於國家的富強不僅無益而且有害。一則因爲它們減少了農戰的人數,二則因爲它們使人驕奢、姦偽、怯弱、畏難。所以他認爲統治者應該以法令一方面禁止這些價值和目標,一方面鼓勵甚至迫使人民從事農戰。 爲了達成這二個目的,秦孝公採納商鞅的看法之後發布的第一條法律便是驅民於農的「墾草令」。但是法令發布後未必能爲人民所遵行,因爲「民之外事莫難戰,民之內事莫苦於農」,統治者要驅使人們去流血流汗必須有一套鼓勵的辦法。依據商鞅的理論,首先統治者必須了解人們的心理,知道他們的好惡。但是其目的並不在聽順民意而投其所好,去其所惡,因爲人民過於愚昧,「閽於成事」,「可與樂成」,而「不可與慮始」。統治者既以其獨特之智「見於未萌」,而欲「論至德」「成大功」,就該「不和於俗」,「不謀於眾」,逕行其是,而使人民順從。因此商鞅所說的探知民之好惡是別有用意的。說穿了就是要知道如何利用人民的好惡,進而控制他們的行爲。 在商鞅看來,一般人都厭惡羞辱苦勞而喜好名利逸樂,要不要做某一件事,大多決定於計算之心。所以如果統治者以厚賞鼓勵從事農戰,以重罰懲創逃避農戰,一般人計算得失,大多會「犯其所苦,行其所危」而去從事農戰。此外商鞅認爲如果能夠更進一步禁止以農戰以外的途徑取得名利,「塞私道」而「啓一門」,其效果就更好了。 爲了實現此一辦法,商鞅建議了許多具體的措施,包括禁止官吏「博聞辯慧」禁止人民受雇於官吏商賈、加重商賈各種賦稅、禁止人民擅自遷徙、廢除旅舍使「逆旅之民無所於食」等等。 以上所述可以說是商鞅的立法方針及若干具體法案,因爲他重視法律,認爲法律可以改變人們的行爲和國家的命運,所以他對法律的性質、功能以及立法和司法的技術,都有相當深入的探究。 商鞅認爲法律的功能在定「名分」。他所謂的名分,就是每一個人或事物特定的地位和歸屬。他說野外的兔子因爲名分未定,「堯舜禹湯且皆如焉逐之」,市上的兔子則因「名分已定,貧盜不取」,又說「以下爲上」也是名分不定,所以認爲名分定則「勢治」,名分不定則「勢亂」。 定「名分」之事基本上就是立法的工作,依照商鞅的主張,應該完全由統治者專斷。如果立法之後又聽任下民議論其是非,則名分仍然不定,將使「姦惡大起,人主奪威勢」以致「亡國滅社稷」,所以商鞅強調明主之國法令既立,「言不中法者不聽」,「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辨慧,不能以一言枉法」。 問題是統治者所立之法是否絕無可議之處?如前所述,商鞅認爲統治者立法並不須要依據民意,此外他也沒有提到任何高階的準則如天志、道德等等作爲法令的基礎。萬一法令並不十全十美該怎麼辦?對於此一問題,他不僅沒有答案,而且根本沒有提起,因爲他的整套理論是以聖君在位爲前提的,聖君所立之法當然十全十美。 法律既爲定分,使人人皆安分守己,就應該使人人都能了解。如其內容過於深奧繁雜,必待賢者而後知之,便不可以爲法,因爲民不盡賢,所以商鞅說「聖人爲法,必使之明白易知」。 爲了使人們易於知曉法令,商鞅訂定了一套法律教育的辦法一先令各級法吏研讀法令,並加考試,然後由他們答覆吏民有關法令的問題,據實告以法令,並將此問答作成「券書」,一給問者,一留政府,作爲證據。這種法律教育雖然很簡單、很機械,但是甚有必要,因爲法令雖然明白易知,沒有加以詮釋、討論的必要,但是法令既是統治者所立,並非必有情理、道德的基礎,人們無法探求其內心或從傳統的德育裹找到法令的準則,所以必須依賴特別的法律教育。商鞅強調此種教育,不是沒有緣故的。 普及法律教育有許多好處:人人皆知法,便應該知道「避禍就福,而皆以自治」,非但「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」,而且「吏明知民知法令也,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」,萬民乃「無陷於險危」。 然而這畢竟只是理想,因爲人們未必都能理性地知所避就,難免有人知法犯法,所以還要有人司法才行。 司法的工作就是以法令去度量一個事件是否合乎既定的名分。在商鞅看來,就像用權衡去稱輕重,用尺寸去量長短一樣冶乎原定的輕重長短者爲是,不合者爲非。因爲所用的是一種客觀的準則,使用的時候十分方便,所得的結果十分精確。他這種將法令當作「械數」的看法,是儒家最感不滿的。荀子曾特別對此加以批評,指出人情萬變,而法令難免疏漏,在許多情形沒有法令可以完全妥當地適用,必須對現有的法令加以詮釋或類推才行,所以司法之人必須知道「法之義」(即其宗旨和精神),才能據而「議」定法的適用。「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〔將法看成測量的器械,斤斤計較其文字度數〕者,雖博,臨事必亂」。不過這種批評是商鞅不願接受的,因爲他正想使法律成爲械數-種簡單的客觀的準則-似免被人濫用。 爲了要使法令發揮其械數的功能,司法者就該將它奉爲唯一的準則,「言不中法者不聽,行不中法者不高,事不中法者不爲」,絕對不可在度量事件之時,又以道德、禮俗,如「禮樂、詩書、修善、孝弟、誠信、貞廉、仁義、非兵、羞戰」等等,作爲準則,去度量同一事件,以致無法斷定其是非。商鞅稱這些法令以外的準則爲「六蝨」,說「法已定矣,而好用六蝨者亡。」他這種看法與儒家之將法律視爲低階準則不同。儒家並沒有說不可用法,而只說法應在德、禮之後適用。他則不僅認爲法以外的準則不可用,並且加以鄙棄。雖然他並沒有聲稱要廢除那些準則,但是後來韓非主張「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,以法爲教;無先王之語,以吏爲師」,「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執於法」以及李斯的焚書坑儒,都是同一種看法自然發展的結果。 除了法以外的準則,司法者個人的好惡也應該排除,不許它們來影響他對事件的判斷。所以商鞅說「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己也」 司法者應該摒除一己的好惡,當然也應該摒斥少數人的「私議」,因爲這些私議皆出於各人的好惡,有害於法令的客觀公正。 總之,商鞅認爲法令既立,便當獨尊,不可另用其他準則,使法令無法確實施行。然而要避免「六蝨」、「喜怒」和「私議」很是不易,所以商鞅慨嘆「國皆有法,而無使法必行之法!」 以上是商鞅所說司法者應該如何慎己,此外他又提出了一些司法者應該如何待人的原則。第一是不能將人民假設爲良民,而應將他們都假設爲姦民。假設人民都是良民,司法者就易流於疏忽,人民就易於犯姦;假設人民都是姦民,司法者就會嚴加防範,人民就不敢,至少也不易犯姦。所以他說「以良民治,必亂,至削;以姦民治,必治,至強。」 這一基本假設是十分特別的。在其他各家裹,荀子雖然有性惡之說,但是在其政治思想和法律理論裹,並沒有將人都假設爲姦民。因爲商鞅有了這樣一個特別的假設,所以發展出了若干特別的司法理論。第一是司法者應該「刑不善而不賞善」這一點與當時一般人認爲司法者應該「賞善罰惡」的想法頗爲不同。在他看來,既然人民都是姦民,司法工作的重點應在索姦和懲姦,而不必賞善。更重要的是因爲他獨尊法令,鄙棄其他的準則同,所以認爲人民只須奉法守令,此外並無其他善行可言。而奉法守令既是人民應做之事,就沒有獎勵的必要,所以他說「賞善之不可也,猶賞不盜」,因而王者「求過不求善」,「刑九而賞一」。 王者刑九而賞一,所賞的是什麼?此前已經提到爲了鼓勵人們遵循統治者所定的導向,追尋統治者所定的價值,商鞅主張刑賞二柄並用,而主要在用賞。但是在司法上他僅提到「賞施於告姦」,鼓勵人民互相監視,勇於舉發。孔子對此一政策的弊害,曾有精闢的批評。但是法家無見於彼,商韓皆以此術爲其司法要訣。商鞅的理由是,「國皆有禁姦邪、刑盜賊之法,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之法。爲姦邪盜賊者死刑,而姦邪盜賊不止者,不必得也。」鼓勵告姦便是要使姦邪盜賊必得。 鼓勵告姦豈不也鼓勵人們擅自判斷他人行爲的是非?商鞅有見於此,但並不介意。他說:「有姦必告之,則民斷於心」,但是只要法令明白,「上令而民知所以應」,並不會出什麼問題,所謂「治明則同」,告姦者據以判斷的準則是與法令的規定相同的。所以他說:「王者刑賞斷於民心……治則家斷,亂則君斷。治國者貴下斷……故有道之國,治不聽君,民不從官。」 但是如果必待姦邪盜賊發生之後才行舉發並處罰,未免已嫌過遲。所以商鞅又主張要「刑用於將過」,就是對於尚未實際犯法之人加以處罰,以達到最大的阻嚇效果。他說:「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,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。治民能使大邪不生、細過不失則國治,國治則必強。」至於如何才能刑於「將過」,他沒有解釋。大約除了有賴司法者洞察之明以外,就要依靠告姦了。 關於用刑,一般的看法是「過有厚薄,刑有輕重」。但是商鞅認爲「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」一罪責與刑量相當,企圖犯罪之人計較得失之餘覺得並無遺憾,刑罰就失去了嚇阻的作用,該人就放心去做了。所以商鞅認爲行刑應「重其輕者」並且要「重刑連其罪」,施行連坐之法。他強調這些措施之目的「非求傷民」,而在「禁姦止過」,因爲罪輕刑重,人民計較之後不敢以身試法,就不去犯罪了。人不敢犯輕罪,當然更不敢犯重罪了。既然「輕者不至,重者不來」,刑罰便不必真正使用,這就是所謂「明刑不戮」,「以刑去刑」。這種想法是商鞅理論的另一個特別之處。後來韓非承此而提出了著名的「民不躓於山而躓於垤」的譬喻。但是二人的推理都很勉強一輕罪重刑可能使人格外挺而走險,何況刑罰至重不過一死,濫刑之餘民不聊生,死何足惜?老子說「民不畏死,奈何以死懼之?」不知商韓如何答覆。 爲了使刑罰有嚇阻的效果,另外一個要件是必須使其適用公平普及,沒有偏頗差別,所以商鞅主張「壹刑」,他說:「所謂壹刑者,刑無等級,自卿相、將軍以至大夫、庶人,有不從王令、犯國禁、亂上制者,罪死不赦。有功於前,有敗於後,不爲損刑;有善於前,有過於後,不爲虧法。忠臣孝子有過,必以其數斷之。」如果真能這麼做,特別是如能行刑不避親貴,對於一般人當然會有極其深遠的影響。商鞅指出周公誅管蔡,晉文殺顛頡,而致於大治,其說太過簡易,但並非毫無道理。問題是他的「壹刑」只及於卿相、將軍以及大夫、庶人,沒有提到君主也該遵守同一法令。<韓非子>內提到若干故事,都顯示君主以及儲君都不與臣民同受法令的約束制裁。這是法家「壹刑」論的致命傷。 但是商鞅仍然強調只要實行了他關於立法、司法的種種建議,吏民一概遵守法令,人人都能確當地判斷是非,各守本分,避禍就福,整個社會就像一部設計精確,運轉順暢的機器一般,很少須人操縱,以致於人主可以「處匡床之上,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」。這種「無爲而治」的狀況,乃是中國古代諸子共同的理想。商鞅治秦之後四五十年,荀子訪秦,見到其朝廷「聽決百事不留,恬然如無治者」,似乎已經近於這一理想了。 秦國能夠有此成就,原因當然很多,其過程也極不易。關於此一過程,商鞅曾有分析:以上所說的立法、司法,都不是困難之事,最困難的是如何使人民接受統治者的法制,尤其是像孝公與商鞅想建立的新法制,因爲任何改革都會受到舊勢力的阻撓,統治者建立新法制之前,必先加以克服。商鞅稱此工作爲「制民」,他說「昔之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」 怎樣才能「制民」?商鞅建議應先使他們「愚」、「弱」、「貧」、「辱」因爲「民辱則貴爵,弱則尊官,貧則重賞」,「愚則易治」,「民弱國強,國強民弱」,「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」。 怎樣才能使人民愚、弱、貧、辱?商鞅主張要禁止他們從事學問、技藝、商賈,而迫使他們從事農戰。「農之用力最苦而嬴利少」,從事於此的人皆因陷於貧困而自感卑微,而且因爲日夜辛勞不息,無暇於學問,與外界也沒有什麼接觸,自然就變得「愚農不知」,「樸而可正」了。除了農墾以外,戰爭也有此一功能,因爲士卒皆受嚴格的軍令控制,「拙無所處,罷無所生」,「從令如流,死不旋踵」,其愚、弱、貧、辱可以說是無以復加了。 其他諸子當然也談統治者應該如何使人民順從,但各家建議的方法不同。商鞅之說與孔子的「富之、教之」固然南轅北轍,與墨子的「兼愛、上同」也杆格難容。老子說「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,將以愚之」,以便於控制人民,使他們盲目地跟隨聖人回歸於「道」,有一點與商鞅的說法相似。但是老子並沒有要使人民貧、弱、受辱,所以商鞅的說法是很特別的。 人民被制服而變得愚、弱、貧、辱之後,統治者便可以很容易地驅使他們,就像牧者驅使被馴服了的牛羊一般。在這樣的關係裹,任何人對統治者只有順從並且爲之服役。(用商鞅的話說就是要「知愚、貴賤、勇怯、賢不肖皆盡其胸臆之知,竭其股肱之力,出死而爲上用」)二者之間沒有相對的權利義務可言,所以商鞅完全沒有談到此一問題。不僅如此,他甚至認爲二者之間連一點恩義也不該有,所以他說:「治主無忠臣,慈父無孝子,無欲善言,皆以法相司也,」這句話聽來又很異常,但卻與商鞅的其他想法是一致的一他否定了道德的價值而獨尊法令(法令本身又不以道德爲基礎)人人遵守法令而生活,就像機器裹的零件一般,雖然互相配合得十分緊密,但沒有什麼恩義可言。這種想法除了老子之外,別家都不能接受。老子則說過「天地不仁,以萬物爲芻狗;聖人不仁,以百姓爲芻狗。」因爲他也只尊崇一個外在的、客觀的自然律-道。這個自然律是與忠孝仁愛等等基於人情的準則是無關的。 總之,商鞅的理論很特殊,很難憑常情去理解。主要的原因就在他要將法令樹立爲最高的準則而排除其他的規範。這是極不自然的,所以他的理論很難爲常人衷心悅服地接受。他自己也有見於此,所以感嘆地說:「聖人治國,易知而難行也!」他強調上下「以法相司」卻又必須一個聖人來立法、司法,而且連聖人都會覺得困難,其說之矛盾,甚爲明顯。 |
| 主题分类 |
社會科學 >
法律學 |